从斗而不破到北京复交:伊朗与沙特百年博弈往事
作者:杨婧格 李文畅 2023-04-06 18:19
虽然两国在对美态度、发展核武器以及教派关系上存在一定分歧,但主权国家理念和厌战思潮的深入人心,这就决定了两国不会将也门和叙利亚等区域的“代理人战争”轻易上升为直接的“热战”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杨婧格 李文畅/文
据相关报道,2023年3月10日,中国、沙特阿拉伯王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其中沙特和伊朗两国在中方代表的斡旋和倡议下,表示愿意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并在最多两个月的时间内重开使馆和代表机构。9天后,伊朗总统莱希又收到了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邀请其访问的信函。
沙特与伊朗的这次和解,既结束了两国长达七年的断交状态,也是中国新时代外交和世界上向往和平力量的巨大胜利。
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沙特与伊朗的这次历史性和解,并非是两国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所能简单概括,还应当从两国交往的历史中加以找寻。
一、巴列维时代的和平
虽然不少文章和著作将沙特与伊朗两国在中东地区的博弈追溯到阿拉伯和波斯民族、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合作与冲突历史,但这种回溯,其实很难完整解释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契合或矛盾点。正如《大棋局》一书作者所认为的——“基于领土考虑的竞争仍在世界事务中占主导地位”,民族或教派矛盾难以主导现代国家之间的交往史。所以对伊朗和沙特两国历史关系的叙述,仍应以一战后两个国家主权建立为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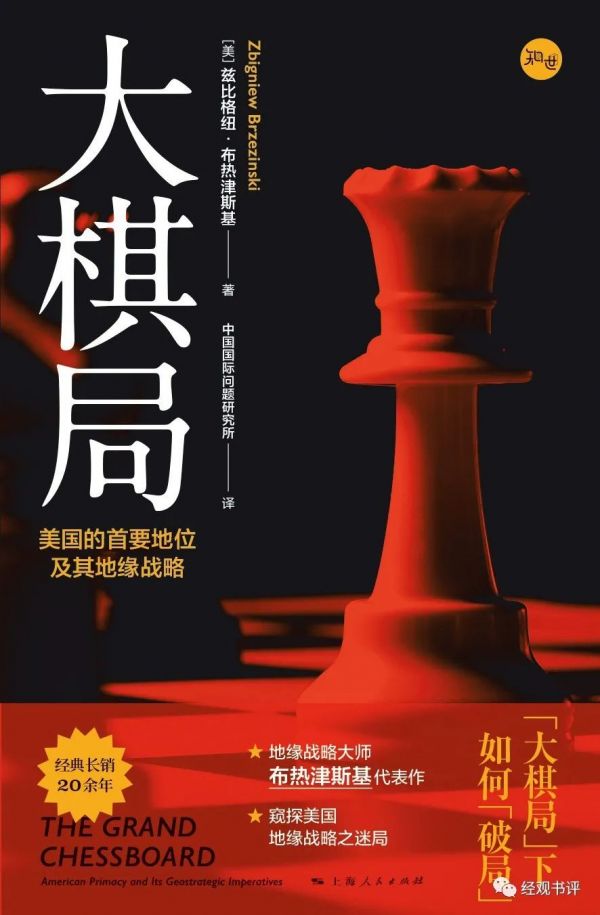
《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1月
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与中东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中东地区的传统格局也迎来前所未有的新变化。而作为该地区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多元。
一战后期,传奇人物伊本·沙特在英国人的拉拢援助下,与奥斯曼帝国军队作战,在阿拉伯半岛中部的绿洲地带迅速崛起。战争结束后奥斯曼土耳其的力量退出半岛,沙特家族又战胜试图独占胜利果实的侯赛因家族,并于1927年建立沙特阿拉伯国家(1932年正式确定国名为“沙特阿拉伯王国”)。而在这一时期,伊朗的恺加王朝也被礼萨汗领导下的军人集团所取代。伊、沙两国新政权陆续建立,并开始接触。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又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1929年—1979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两年后与伊朗巴列维王朝缔结友好条约,开启了现代伊朗与沙特双边关系新阶段,此阶段两国虽偶有冲突,但总体关系较为友好。
1979年—1989年,伊朗巴列维王朝在国内教俗变革力量的联合打击下倾覆,国王出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应运而生。伊朗新的当政者霍梅尼对沙特态度强硬,致力于对外“输出革命”,使两国关系逐渐走入低谷。
1989年至“阿拉伯之春”前后这段时间里,最高领袖霍梅尼逝世后,伊朗领导人开始奉行务实主义外交政策,积极与包括沙特之内的各邻国建立起合作友好的新型外交关系,两国关系趋于缓和,呈现出曲折发展但“斗而不破”的新趋势。
从沙特建国到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的半个世纪时间里,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外交关系经历从无到有,合作的愿望大于对立冲突。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分别奉行着伊本·沙特的“和平中立外交政策”与礼萨汗的“睦邻友好,建立良好周边环境的原则”,二战结束后两国都曾奉行亲美外交,在抵制苏联影响,共同宣扬伊斯兰世界观等方面进行过合作。当然,双方也曾在朝觐、波斯湾岛屿归属以及阿以冲突等问题上意见相左,但总体上并无大的利益纠纷。冀开运教授在《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一书中认为,1929年—1979年之间的沙伊关系,属于典型的常态化外交。

《伊朗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研究》
冀开运/著
时事出版社
2012年9月
沙特与伊朗两国外交关系的确立并不容易。20世纪30年代以前,由于沙特阿拉伯经济落后且伊朗认为沙特对伊斯兰教圣地采取轻视态度等原因,拒不承认沙特阿拉伯的合法地位,直到1929年双方才签订《沙波两国友好条约》(当时伊朗叫做波斯),1929年也被认为是沙伊外交开始的起点,开启了两国曲折复杂的深度交往。在此之后直到二战前夕,两国关系未出现大的波澜。二战结束后,冷战格局迅速形成,美苏争霸的气氛扩散到了中东地区,伊朗与沙特阿拉伯意识到苏联南下对国家政权与思想的威胁,都选择与美国接近,共同抵制苏联对中东地区的力量渗透。亲美外交的开展,促成了沙伊两国元首的互访和双边关系的升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埃及和伊拉克等国先后发生推翻王权统治的军人革命,纳赛尔等政坛新秀鼓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哈全安教授在《中东史》一书中分析道:“纳赛尔政权宣称,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革命将是实现阿拉伯民族统一的基础,进而将攻击矛头指向阿拉伯世界的诸多君主国家,甚至不惜诉诸武力”。这势必对沙特阿拉伯王国和伊朗巴列维王朝的政体合法性形成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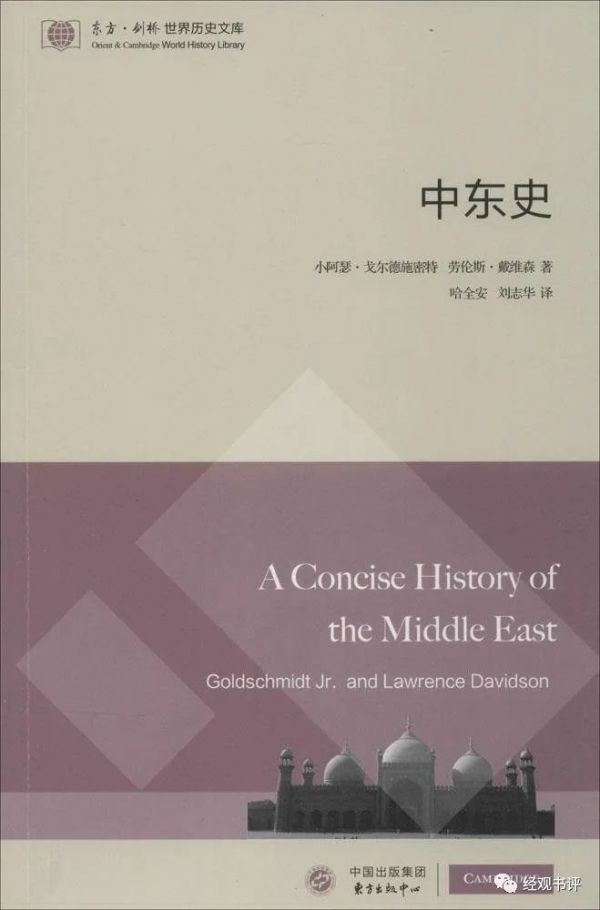
《中东史》
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 劳伦斯·戴维森/著
哈全安 刘志华/译
东方出版中心
2015年4月
沙伊关系发展又出现了新趋势,两国为了共同对抗埃及领导下的“泛阿拉伯主义狂潮”,一同加入了石油输出国组织,这使得两国关系到达新高度。沙特阿拉伯积极贯彻强调宗教认同的外交政策,这一点在费萨尔上台后首访伊朗一事上就能很好地体现出来,而伊朗对沙特新国君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表达出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友好愿景,也足以说明沙伊关系在此阶段稳中向好发展。
20世纪70年代,沙伊两国关系延续了之前以合作为主的发展态势,如两国在伊拉克问题上进行合作,沙特还曾暗中支持伊朗颠覆伊拉克政府的计划、沙伊共同帮助海湾国家抵御左派影响等。在这前后,虽有诸如1943年的朝觐事件,有1955年伊朗加入巴格达条约引起沙特不满等不愉快事件,但不影响两国之间和平交往的基调。
二、霍梅尼时代两国关系的破裂
在沙特和伊朗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友好交往后,反巴列维王朝社会革命的爆发与紧随其后的霍梅尼领导下伊朗伊斯兰政权建立,打断了这一趋势。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到1989年霍梅尼逝世这十年间,伊朗的外交政策一直严格遵循最高领袖霍梅尼的激进主义原则,而这也是由于美国及其盟友为扼杀新生的伊朗政权而加大了对伊朗的遏制力度所致。作为在政治、经济上和美国有密切联系的沙特,自然也难以置身事外。
首先,霍梅尼思想在当时的伊斯兰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蒋真教授在其《后霍梅尼时代伊朗政治发展研究》一书中指出——霍梅尼的政治思想的首要内容就是反对君主专制。霍梅尼主张建立伊斯兰共和政府并指出“我们需要的伊斯兰政府将是宪政的而不是专制的”,这也就代表了伊斯兰革命对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君主国的政治根基造成了直接威胁。

《后霍梅尼时代伊朗政治发展研究》
蒋真/著
人民出版社
2014年9月
其次,在两伊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六国在沙特呼吁下建立起了海湾合作委员会,以此共同抵抗伊朗革命影响的外溢。两国在战争最后阶段甚至一度断交。
最后,双方在民间朝觐问题上也出现严重分歧。霍梅尼认为朝觐不仅是宗教事务,更是政治事务,并主张通过朝觐来输出伊斯兰革命。这种观点引起了沙特官方的强烈不满,最终在1987年酿成流血事件:伊朗朝圣者为响应霍梅尼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号召,在圣地麦加举行示威,受到沙特警察的制止,随后演变成大规模冲突并导致人员伤亡。
事件发生后,双方各执一词,说法不一:沙特方面认为这是伊朗官方授意下的暴乱活动,属于伊朗革命卫队和政府长期策划的阴谋;伊朗方面则表示此事件是沙特政府预谋的对群众的谋杀,并认为最先使用暴力手段的是沙特警察。该事件最终导致了本就不稳定的沙伊关系暂时破裂,两国于1988年断交。1987年麦加朝觐冲突对两国从官方到民间的交往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附带一说,2015年两国围绕麦加朝觐冲突再起,再度导致两国加速走向决裂。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第一个十年的沙伊关系以激进和紧张为主,这与巴列维王朝统治时期的沙伊关系存在不小的差异。伊朗与伊拉克长达八年的战争加剧了沙特的不安,两国意识形态的分歧也使得双方在和平交往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总体来看,沙伊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可以用“剑拔弩张”来概括。
三、从关系回暖到断交危机
在霍梅尼逝世后,伊朗处于两伊战争结束的恢复期,战争给伊朗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国力下降迫使伊朗高层通过缓和对外关系来争取稳定的外部环境。卢红飚教授在《解析伊朗与沙特关系的阶段性特征》一文中曾指出:在此阶段,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逐渐让位于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伊朗将改善与邻国沙特的关系作为外交重点,沙伊关系开始趋于缓和并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在“后霍梅尼”时代,伊朗整体上奉行务实主义外交原则。时任总统拉夫桑贾尼曾说:“目前这个时代是建立国际组织和国际关系的时代,如果我们中断了这种联系,就无法生存,我们不应该无缘无故地树敌。”
拉夫桑贾尼的言论暗示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存在巨大空间。而沙特也公开释放缓和信号,表示希望与伊朗在各方面改善关系,并恢复两国正常外交。沙伊两国的关系在经历1988年断交的冰点后,逐步开始回温。
1991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出兵突袭科威特,让伊拉克瞬间超越伊朗,成为沙特周边地区最大的威胁。伊朗也抓住这个机会力挺被侵略的科威特国家流亡政府,并接纳数万名科威特难民。由于科威特是沙特在阿拉伯半岛乃至中东世界重要的追随者之一,伊朗此举明显有利于间接改善和沙特的关系。在萨达姆的“助攻”下,沙特与伊朗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并随之进行了一系列高层互访。两国在朝觐人数、海湾安全和调解教派冲突方面都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了初步共识。1995年,沙特王储阿卜杜拉掌权后,更加积极地寻求与伊朗改善关系,并与伊朗上层官员会面传递友好信息,后续两国的高级官员互访也愈加频繁。
进入到21世纪,两国之间的关系因美国扩大在中东的军事行动而出现新的隔阂。如2003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在美军攻势下倒台后,得到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政治势力达瓦党等迅速崛起,填补了美军占领时期的政治空间。什叶派在伊拉克的得势引起了包括沙特在内诸多阿拉伯逊尼派国家的不安,进而影响到回温不久的两国关系。
此时的沙伊关系,变得更加多元复杂。结合在冷战结束后世界发展呈现多极化的大背景,王光远教授在其著作《沙特与伊朗关系研究》中强调:尽管此阶段沙伊两国之间已暴露出新的问题,但两国领导层都在尽力避免两国关系紧张化,并为此做了许多努力。如在此期间,伊朗贸易部长召开招待会,声明两国近年来在经贸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沙伊签署《沙伊海运合作协议》以扩大双方货运贸易额。双方政治领域的剑拔弩张,并未影响到经济合作的扩大,即便是在政治上,沙伊两国政治精英也在保持对话沟通。如2007年,伊朗总统艾哈迈德·内贾德与和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实现会晤,希望为地区分歧找到合理妥善的解决办法。

《沙特与伊朗关系研究》
王光远/文
时事出版社
2018年8月
由此可见,在沙伊关系迈向新阶段的过程中,巩固来之不易的和平状态尚为双方高层共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此时期的关系缓和,并非是两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取向达成一致的原因,而是两国历届领导人奉行务实政策、避免双方关系再次陷入僵局的结果。
不过,作为“地缘战略棋手”之一,伊朗并未因为同沙特关系的改善而放弃对沙特周边国家内部什叶派武装(如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巴林等阿拉伯君主国内部什叶派民众为争取平等权利而开展的街头运动,也不时得到伊朗官方的肯定与声援,引得约旦国王惊呼“什叶派新月地带”已经出现。这些都让作为阿拉伯君主国和逊尼派世界领头羊的沙特阿拉伯如芒在背。
“阿拉伯之春”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沙特对于伊朗这一地区秩序挑战者的不安全感,最终导致双方在2016年断交。
进入2011年后,西亚和北非的许多国家爆发民众抗议威权政府统治的社会事件。原先扮演阿拉伯国家“领头羊”角色的埃及和伊拉克受困于动荡的内政,国力倒退,难以承担维持区域政治秩序的角色。相比之下,沙特则因为石油经济的繁荣和内部稳定的政教结盟关系而扛过了这一轮冲击。并以“海合会”的名义和阿联酋联合派出两千人的地面部队到巴林,协助该国王室弹压其国内的什叶派抗议活动。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沙特阿拉伯出钱出枪扶植叙利亚国内反对派,与伊朗支持下的阿萨德政权进行对峙。2015年萨勒曼继承沙特王位后仅过去两个月,就派出空军轰炸得到伊朗援助的也门胡塞武装,并逐步上升为大批地面部队的进驻。
相比于1991年海湾战争时期依赖美国军事支援的状况,此时的沙特政府已改变消极守势,在同伊朗的中东博弈中趋向强硬。而伊朗也不甘示弱,对外继续通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组织向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等国家的什叶派政治势力提供支持。对内则加快核武器的研制工作,这也使其遭到包括沙特在内多国的制裁或抵制。
对于伊朗的“拥核”计划,美国一直尝试通过制裁和对话双管齐下,最终实现对后者的制衡。在美国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个任期内,与伊朗对话解决其“拥核”问题占据上风,并于2015年7月达成了全面协议。伊朗以减缓研发核武的速度,换得了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对其部分制裁的撤销。
然而,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传统盟友沙特来说,美国与伊朗的暂时和解使原先致力于扮演美伊两国冲突调解者和获利者角色的利雅得当局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并促使沙特开始探索一条摆脱美国影响的外交道路。2016年,沙特不顾伊朗和美国官员反对,执意处决其国内什叶派异见人士尼姆尔,直接导致伊朗国内民众愤而冲击并焚烧沙特阿拉伯驻德黑兰大使馆和马什哈德领事馆。尼姆尔虽为沙特公民与阿拉伯人,但其在中东什叶派内部享有较高威望,甚至连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都曾在2014年为了他的生命安全给沙特王室写信求情。伊朗如此看重的一个人被沙特处死,这也成为了压垮沙伊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6年1月,沙特以驻伊朗使馆遇袭为由,撤回外交人员,与伊朗正式断绝外交关系。此后双方在伊拉克和阿曼等国斡旋下重启和平接触。用范鸿达教授接受文汇网记者采访时的话讲,直到今年3月,伊沙双方才找到了北京这一“更有实力和影响力且双方都能接受的调解者”,完成了两国关系根本改善的临门一脚。
回顾伊朗与两国在中东的百年博弈历史,我们将会发现,虽然两国在对美态度、发展核武器以及教派关系上存在一定分歧,这些矛盾甚至有可能借助偶发性的争端而演化为断交危机,但主权国家理念和厌战思潮的深入人心,使得两国在交往中仍应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这就决定了两国不会将也门和叙利亚等区域的“代理人战争”轻易上升为直接的“热战”,两国关系虽起伏不定,但始终存在着改善回暖的广阔空间。正如前沙特国王法赫德所言:“伊朗是伊斯兰国家,在同一框架下的相互合作,符合两国的利益”。未来的沙伊关系发展走向尚难定论,但“斗而不破”显然比公然断交要具备更大的调试空间。
(两位作者系辽宁大学世界史研究生,本文为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和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亚洲问题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相关热门新闻
请点击 添加到主屏幕
添加到主屏幕

